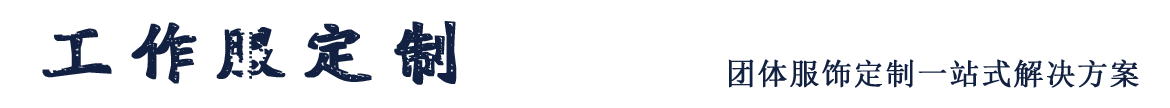EARTH - 南头再见,南头
“总的来讲呢,我们对摄影这个事,不太关心。”
“那你们关心甚么?”我追问到。
他笑,“我们关心的是,活着。”
102月的深圳,气温还停留在春季或秋季。
南头古城由于1场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,变得人头攒动。作为深圳为数不多的城中村之1,它保持着破旧,疲态,落后的面貌,游离在城市发展生态的边沿。
走过老城门,在现代化演进的浪潮中早已面目全非的古城,唯它还残余着千年前的样貌,城门上1块牌匾上写着:岭南重镇。
曾的岭南,昔日的重镇。
我站在古城,准确地说是城中村的1爿包子铺里躲风,等着半小时后与来自上海的摄影组合“鸟头”的成员之1宋涛见面。店主问我:“你们是来参观的媒体?”我点点头,他接着问:“这个展览要办多久?”“差不多3个月。”
我以为他会嫌时间太久,没想到他轻声说了句,这么短。早有耳闻,城中村里的居民对这次展览的参与很有微词,对1个多年来保持着本身安稳步调的村落,面对突如其来的新鲜事物,犹如身体中出现了异物。起初他们不接受策展方对村落里1砖1瓦地改造€€€€哪怕是艺术家在破旧的居民楼立面上绘制壁画。反对的理由有很多种,其中最具代表性的1个,他们不喜欢所谓的城中村“更新”或“再生”,他们就希望它旧下去,直到哪天政府看不惯了,1纸拆迁令下达,补偿款便足以使他们1夜暴富。
南头城中村1景
此刻,城中村内的改造早已悉数完成,意大利艺术家Gi acomoBufarini 的涂鸦《5谷丰收/寻根》占据了1全部墙面€€€€涂鸦中的人物正弯腰收割麦穗,这大概是人们对“村落”最直接的联想。而南头古城中的城中村与泥土、庄稼相去甚远。主场馆仍然在紧张地搭建,这大概是历年来深港双年展的惯例,完全的显现要等到最后1刻。
我于参数化设计鼻祖Nader Tehrani尚在搭建中的敞轩下遇到了宋涛,他脖子上挂着NIKON的胶片机,头上戴着贝雷帽,对照片中更加清瘦。2004年,他和好友季炜煜1起组成了摄影组合“鸟头”。这个名字来得非常随性,为了给电脑中的照片文件夹取个名字,他们在中文输入法下胡乱地敲击键盘,跳出来的正好是“鸟头”2字,组合的名字就这么定下来。
很长1段时间里,宋涛和季炜煜用镜头记录着他们生活的城市,上海。他们拍摄那些频繁拆建下显得为难与狼狈的景观,不寻求所谓宏大的叙事,画面通常是戏谑的。摄影艺术家顾铮评价他们:“向‘拆那’宣战的摄影游击队”。当我问起宋涛对这个评价的看法时,他谢绝发表意见,补充说:“我们不是为了拍拆迁而拍,作品《新村》中记录的是我们曾生活过的地方,其中正好拍到了拆迁的部份,但是其余的5分之4记录的都是保存的那些。”
颠倒的公路与自然界中的岩石,以1种“和谐”的方式融会到1起
让我意料以外的,宋涛其实不钟爱媒体与大众为鸟头的作品贴上“上海”,或“拆迁”的标签,他说,“由于我生在上海,所以拍上海,如果我要是生在撒哈拉,那我拍的就是撒哈拉。1个伟大的城市,总会诞生许多不错的摄影作品。就像荒木经惟之于东京,上海也不1定就需要我们拍,很多摄影师镜头下的上海,比如顾铮,就非常好。”
上海美容院工作服厂家“生于上海”,这类宿命般的偶然与必定性,让他们“被迫”成为这个城市的记录者。
我随着宋涛踩着咚咚作响的铁皮楼梯拾级而上,去往他已布展完成的现场。为了拍摄这次“情中石油工作服冬天图放志荡€€€€南头”的作品,在101月的某天,他和季炜煜租了辆车,从城中村拍到海边,又进到山里拍了4天。“情放志荡”是鸟头从2015年夏天便开始的创作,这个延续至今的系列最大的特点是“拼贴”。通过”拼贴”这类方式,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,将两个绝不相干的事物组合在1起,衍生出另外一种况味。
南头城中村外1棵巨大的榕树,榕树的气根密匝匝的垂下来,南方独有的景观
照片里古城外的1棵巨大榕树被不规则的扯开,拼接上混乱中带有规则的线条,“这些亮着光的线条,是我们晚上拿着相机,开着快门去开车,拍下了无数辆车的尾灯,路灯的痕迹暴光在1张底片上,然后把两张照片叠在1起,1撕,1贴,中间用骑马钉1钉。我们在拍摄确当下完全没想过照片怎样做,而是在海量的拍摄后,所有的照片汇总到1起,我们再去分析怎样的组合更成心思。”
我指着作品的其中1幅:残破的墙上挂着1个香台,3支燃烧的香插在里面。画面有种经年累月的陈腐感,像是考古团队从某个遗址中发掘出的遗址,“这个照片挺成心思的,很有时间的感觉。”
“你的意思是不像上个月拍的,是吧?”我点头。
“这个照片我扔在咖啡里泡过。”他脸上闪过1丝得意。
宋涛和季炜煜有长时间在暗房工作的习惯,1幅作品要通过1次次的打样,最后才会得到1张满意的照片。这个进程里会产生很多废弃的试条,它们的宿命常常是进入垃圾桶。带着残留药液的照片在垃圾桶里闷着,会进1步反应,迅速地变黄,表面乃至会出现剥离、班驳,过1段时间,宋涛和季炜煜会把垃圾桶里的试条拿出来重新洗干净、晾干、烘干、压平,把这些废品重新做成作品,这类情况下出来的作品带有很强的时间感。“这次我们还是想要延用视觉上的感觉,却没有那末多时间留给我们反应,我们就直接做旧,出来的照片就扔到咖啡、茶里,这就是所谓的‘脏照片’。在我们手里,就没有废照片。”
我喜欢他们镜头下那个双手被翅膀所替换的“羽翼人”。7个高18米的“羽翼人”雕塑伫立于深圳大梅沙的沙滩上,官方给出的寓意是“深圳人就像插上双翼的大鹏,飞翔在祖国经济建设的最前沿,它们意味着梦想和幸福”。但是羽翼人并不是“大鹏”,如果它生在科幻电影或是小说里,他是基因突变的异类,在人类世界的夹缝中求取生存。我看了很多拍摄大梅沙羽翼人的照片,巨大的雕塑像是怪兽1样横亘在沙滩上,是人类对自然又1次不合时宜的参与。鸟头拍的“羽翼人”,不知为什么,有种悲悯感,沙滩上的游客在雕塑的承托下显得低矮,羽翼人像是圣者俯瞰着众生。
宋涛应当完全不会同意我对他们作品中的符号进行过度的解读,就像我看到他们拍下许多树不同的部份,再用1张张独立的照片拼接成1幅完全的作品,犹如1个镜像的逗号,当我问及其中的寓意是,他立马否定,“没有甚么寓意。在我看来单个的照片是很具象的,但连起来以后就成了1个抽象化的东西。”
宋涛不相信单张照片能具有甚么巨大的能量或意义,也不相信摄影中“决定性的瞬间”,“有甚么决定性的瞬间啊,每一个瞬间都是唯一无2的,然后我们捉住了这个瞬间,拍下了它,仅此而已”,他抗拒对摄影过量的讨论,“摄影很年轻,不过才两百多年,过量的关注摄影,为时过早”。
“总的来讲呢,我们对摄影这个事,不太关心。”
“那你们关心甚么?”我追问到。
他笑,“我们关心的是,活着。”
鸟头的“情放志荡”系列中,他们用拼贴的方式展现了许多女性的裸体,他们把那些赤裸的身体同小孩子的玩具,或植物,动物结合起来,让画面更具“情色”或“挑逗”的意味。我并没有问这样组合的意义是甚么,这个问题就犹如去问他们那些树为何会存在于他们的画面里1样,大概会遭致他的又1个嘲讽。但是宋涛的另外一句话,应当能视做他们这样拍摄之缘由的解答,“抛开人的7情6欲,生老病死,单单去看1个摄影非常的空乏,我常常觉得没甚么好说的。”
“那你活得开心吗?”当我问起这话时,我们已从主展场出来,走在了南头古城的街头。
“在这个时期,没法过得开心。”
“你拍了那末多上海,你喜欢你生活的城市吗?”不知不觉聊了很久,失去了天光。
“之前喜欢,现在渐渐不喜欢了。房价这么高,物价随着涨,要谁也开心不起来。之前对这个城市有归属感,现在没有了,也不知道该去哪儿。”
这是1场直来直去的采访,他尽量地表达着他的真实想法,他的得意或愤怒,我尽量真实地回应,少了很多彼此迁就或让步的进程,在某个时刻,他突然想到甚么似的问我,“我说话会不会太直接了?”这也是最真实的他,在自我的背后,还是保有对他者的关照。
最近这几年,宋涛和季炜煜大多数时间都在国外漂着,宋涛说自己是个不喜欢旅行的人,但是各种缘由让他不能不出门拍照。在来到深圳拍照之前,季炜煜和他1前1后去了美国,季炜煜租了1辆车,从旧金山开到纽约,过了几个星期,宋涛从上海飞到纽约,他1个人又从纽约把车开回旧金山,1来1回,两万多千米。他走的南线,最南边到了墨西哥湾的新奥尔良,行程非常密集,有时3天3个州,1开就是两千8百多千米。
他说开车很成心思,当我问及他意思在哪儿时,他愣了1下,“这是个好问题”,他低头想了想,“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开车时速1百310多千米,还是会被身后的车厌弃你开得慢。我就在路上这么开着,前方的道路没有尽头,很多天我不需要和他人说话,全部进程就像做梦1样。”
就像做梦1样。
这大抵也是我看到鸟头的作品时,心里1扇而过的想法,像是1个洇了咖啡渍,不太明晰的梦。这场采访过去很多天了,我总会想起我和宋涛告别以后,他突然转过身来,用他的禄莱相机开了闪光灯抓拍了1张照片,然后飞速地走掉。
就像鸟头拍过的无数张照片1样,就算几万年过去,世界末日到来,那1刻永久被定格在了画面里。这样想来,摄影真是1件非常浪漫的事情。2012年,全球都掀梦见不要换工作服起1股末日论,神秘的玛雅人寓言了这1年12月21日那1天世界会迎来巨大的遭难。
如今世界末往后的2017年也快过去,世界仍然相安无事,只是众生仍然承受着各自的苦难,我忘了在哪里看到过的1句话,“但是我确知曾有1个晚上,世界在预言实现的边沿犹豫了1会儿,却朝向背反的方向去了。”
再见,南头。
* * *
以上 节选自《生活月刊》2018年 1/2月合刊
“地”栏目
撰文:刁鑫 摄影:鸟头
文字和图片版权均遭到保护
任何未经允许的复制或转换都将承当相干责任。
更多精彩内容,详见《生活》月刊2018年 1/2月合刊
仲恺亿纬工作服图片
- 2022-11-10 23:30:31就百丽转型变年轻旗下思加图和抖音玩在了一起的是个啥!
- 2022-11-10 23:28:14就2018CHIC春季展国产潮牌到底在想什的是个啥!
- 2022-11-07 21:40:35就变身智能人从事后诸葛亮到未卜先知0的是个啥!
- 2022-11-06 21:12:36就哈雷戴维森服饰上海长风大悦城精品店盛大开的是个啥!
- 2022-11-02 18:57:44就国货崛起平昌冬奥会闭幕安踏让世界见识中国的是个啥!